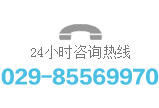1965年,美國著名控制論學者扎德(Lotfi A.Zadeh,1921~)在《信息與控制》(Information and Control)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論文,最早提出了“模糊集”概念,系統研究了事物的模糊性問題,徹底糾正了人們對模糊性的偏見,并把它引入數學中,成功地實現了模糊與數學的結合,誕生了模糊數學,之后又相繼在人文科學領域出現了模糊語言學、模糊語義學、模糊美學等新興學科。“模糊集”理論的提出是一個偉大的科學發現,為人類作出了奠基性貢獻。
在此之前,19世紀德國數學家奧爾格·康托爾(Contor,1845~1918)曾創立了“樸素集合論”,但該理論在定義集合的方法上會導致悖論,為了消除這些悖論,羅素等一批數學家又共同努力,在20世紀初創建了更嚴密、更精致的集合論——公理化集合論。它是微積分理論體系的基礎,對現代數學和邏輯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。然而上述經典集合論卻無法處理模糊的信息和知識,于是這才有了后來扎德創立的“模糊集合論”。
如今,現代科學告訴我們,模糊集理論正以無窮的生命力對各種科學門類施加影響,努力實現與其他科學的結合,特別是人文科學領域。扎德說:“在模糊性起顯著作用的領域里的應用——特別是人文系統,這里人類的判斷、感覺和情緒起著重要的作用。”我們認為,文學翻譯正是人類的判斷、感覺和情緒起著重要作用,即模糊性起顯著作用的領域。今天我們大膽地提出“文學翻譯是一門模糊藝術”這一新的命題,是對扎德“模糊集”概念的一種新認識、新視野,也可以看作是對“模糊集”概念的一種延伸和豐富,同時更為現代翻譯理論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,也是一個新的向度。
現今我們欣喜地看到,模糊集理論在自然科學,如計算機、自動化、信息科學、管理工程、醫學等領域;在社會科學,如語言學、心理學、邏輯學、考古學、圖書館學等諸多學科領域,都顯示了它的極其強大的應用價值。
關于精確與模糊
長期以來,人們在關于精確與模糊的認識上形成了一種系統化的方法論觀點。認為,精確總是好的,模糊總是不好的。越精確越好,精確的方法就是科學的方法,模糊的方法則是非科學的方法,是尚未找到精確方法之前的一種權宜之法。這種對精確方法的崇拜和對模糊方法的否定,一直被人們當作一種真理,從未受到過質疑。
其實,模糊與精確是二元對應,都有它們存在的前提和必要,都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基礎。精確概念固然重要,模糊概念也同等重要,模糊并不是貶義詞。從人類認識活動的客觀機制來說,人們認識活動的多樣性和有效性,往往并不完全來自精確的認識形式和語言表達方式,恰恰相反,是來自各種模糊思維形式和語言表達方式,因為這種模糊思維形式和語言表達方式在人們交往活動中,特別是在知識交流中,更具有完美和高效的特征。正如德國哲學家康德所說:“模糊概念要比明晰概念更富有表現力……在模糊中能夠產生知性和理性的各種活動……美應當是不可言傳的東西。我們并不總是能夠用語言表達我們所想的東西。”波蘭語言學家沙夫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:“交際需要語詞的模糊性。……假如我們通過約定的辦法,完全消除了語詞的模糊性,那么,我們就會使我們的語言變得如此貧乏,就會使它的交際和表達作用受到如此大的限制,而其結果就摧毀了語言的目的,人的交際就很難進行,因為用于交際的那種工具遭到了損害。”因此可以說,我們應該用相反相成的觀點去考察精確與模糊之間的運動轉化規律,從而從模糊論角度去促進精密科學的發展。
而且,模糊是一種境界,是一種高超的境界,這種境界不是藝術世界所專有的,哲學世界以及素以精確著稱的科學世界一旦達到了某種高超的境地,達到了極玄之域,也會呈現出一種“悠然心會,妙處難與君說”的朦朧、模糊。這朦朧、模糊是精確之后,螺旋式上升的朦朧、模糊。它的艱辛歷程是:含糊→精確→朦朧。這時的朦朧、模糊(或含蓄)并不是低級、無知的含糊層次;它是精確的升華,是長期艱苦地向精確化目標挺進之后得到的最高報償。(參閱趙鑫珊《科學藝術哲學斷想》)今天,在翻譯理論與實踐上模糊集論的影響和應用越來越大,而且正在得到迅速的發展,為翻譯學科建設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。誠如扎德所云:“如果深入研究人類的認識過程,我們將發現人類能運用模糊概念是一個巨大的財富而不是負擔。而這一點是理解人類智能和機器智能之間深奧區別的關鍵。”(《模糊集論——展望》)事實上,不僅客觀世界中的客體普遍存在著界限不清的現象,而且人的思想和語言也彌漫著模糊性。
文學翻譯是語言的藝術,也是模糊藝術。由于語言的內涵和外延的變通性較大,因而模糊性已成為語言的一種必然屬性。文學作品都是主體反映客觀事物和對客觀事物的主觀評價,其中也必然蘊育了主體的情感因素,而“情感正是心靈中的不確定的模糊隱約部分”。在客觀事物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這許許多多的不確定性、不明朗性,或亦此亦彼、相互關聯的過渡狀態,都是模糊現象。在文學翻譯中,如何處理這些模糊現象便成了一門藝術。
就文學翻譯中的模糊性而言,主要表現在“語義模糊”和“意象模糊”兩類。它們既造成了翻譯的困難,同時也開辟了廣闊的再創造空間。
關于語義模糊
首先從繪畫與翻譯的關系說起。在中國傳統繪畫理論中有一條藝術規律,叫“似與不似說”,或“不似之似說”,它對繪畫產生著重大影響。中國歷代畫家對此都有精辟的論述和獨到的見解。
明代畫家王紱在談到蘇東坡的“論畫以形似”一詩時曾寫道,此“蓋言學者不當刻舟求劍,膠柱而鼓瑟也。然必神游象外,方能意到圜中。”又說:“今人或寥寥數筆,自矜高簡,或重床疊層,一味顢頇,動曰不求形似,豈知古人所云不求形似者,不似之似也。彼煩簡失宜者焉可同年語哉!”(《書畫傳習錄》)現代大畫家齊白石也說過:“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,太似為媚俗,不似為欺世。”(《齊白石畫集序》)從古代到現代,畫家們對“不似之似說”道出了一個真理。那就是作畫既不能刻意追求真似、酷似,也不能不似,要做到不似之似,即使畫作既有自然的形貌,又有畫家的靈魂,達到物我同一,主體與客體一致的效果。因此說,不似之似,是藝術的最高境界,它體現了哲學上的“模糊美”。
那么,“不似之似說”對翻譯,特別是文學作品的翻譯,是否也是一條適用的藝術規律呢?答案是肯定的。
翻譯家葉君健說過:“文學和藝術作品畢竟不是科學,而是觸及‘靈魂’的東西,這里面有‘朦朧’和‘似與不似之間’的成分,要用像數學那樣精確的形式表達出來是不可能的。這里有一個‘再解釋’的過程。譯者在‘揣度’的過程中,就受到他本人的人生修養、文化和政治水平、藝術欣賞趣味以及他對作者及其時代背景的知識等因素的限制。因此,譯者的個人因素在翻譯工作中所起的作用,是決不能忽視的。”(《翻譯也要出“精品”》)從模糊學角度說,“酷似”與“不似”是兩種狀態,兩個極端,而這兩個極端產生的作品與廣闊的中間地帶產生的各個作品,共同構成一個“模糊集合”。集合中各個元素對該集合的“隸屬度”(“隸屬度”是模糊學中使用的核心概念)是不同的。“不似”隸屬度為0;“酷似”隸屬度近于1。中間屬于似與不似之間的狀態,隸屬度各不相同,也許有的三分相似,也許有的七分相似,都帶有模糊性。從理論上講,不同的隸屬度都可能產生好的作品。作為翻譯,逐字翻譯和自由翻譯恰似繪畫中“酷似”與“不似”的兩種狀態,兩個極端。最佳譯文往往產生于二者之間的中間狀態。
下面,且舉一個具有模糊性的例子。符家欽在《記蕭乾》中說:“喬伊斯故意把英文中yes(是)no(不是)開頭字母互相調換。表面是文字游戲,但錢鐘書在《管錐編》里卻破譯為‘中國有唯唯否否的說法,nes,yo正表達了辯證法中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對立面關系,很有哲學意味。’旨哉斯言。”nes,yo如何譯?譯者蕭乾和文潔若譯文正譯的是“唯唯否否”。既然原文如此模糊、朦朧,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,既然是“是否”之意,那類似的也可譯為“是非”、“有無”之義,如:“無中生有,有中存無”,“似是而非,似非而是”,“是是非非,非非是是”等等,難道這不是模糊藝術的魅力嗎!這不正像譯界常說的一句話:“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”嗎!
關于意象模糊
《周易》指出:“圣人立象以盡意,設卦以盡情偽,系辭焉以盡其言。”魏晉玄學家王弼釋云:“言者所以明象,得象而忘言;象者所以存意,得意而忘象。”(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)從創作實踐來說,“意”就是指作家作為創作主體之“意識”、“意念”、“意向”、“意圖”、“意志”,乃至“心意”、“情意”等。它不一定是明確的理性意識,也可以是一種潛在意識,是理性意識與感性認識的交融,是一種認知與情感的心意狀態。“象”,則是處于感覺狀態的經驗性具象,指反映客觀世界事物的形象。作家將這種“意象”狀態訴諸筆端,便構成文學作品。文學作品有二“忌”。一忌“言征實”,“情直致”,即指語言不可據實,亦不可直瀉情懷。明王廷相解釋說:“言征實則寡余味也,情直致而難動物也,故示以意象,使人思而咀之,感而契之,邈哉深矣,此詩之大致也。”(《與郭介夫學士論詩書》)也就是說,作家不能將創作中的明確的思想傾向直說出來,必須化為朦朧之“意”與象、境結合起來。二忌將作品的深刻哲理直說出來。作品要達到至境,沒有深刻的哲理透視是不行的,這種哲學思想必然巧妙地滲透于意象意境之中,或隱或顯地表露出來。這是隱藏在作品深層的東西,也是翻譯家必須要挖掘和表現的東西。這就是造成作品具有意象模糊性的原因。
翻譯時,譯者從作品提供的意象框架或提示基礎上,在心靈中構建新的意象,這是一個“心靈化”過程,意象正是感性的東西與心靈的東西的結合體。如黑格爾所說:“感性的東西是經過心靈化了的,而心靈的東西也借感性化而顯現出來。”
當然,作品形成的語言文字并不直接構成意象,只是包含在譯者再現這種意象的潛在可能性。語言文字只是一種符號,是負載意象、意境的一種神秘密碼。當意與象、境融為一體時,是朦朧難分的,模糊的。加上語言文字是無生命的,只有經過作家感情、意念的浸染,才使這些本無生命的文字符號仿佛瞬間活躍起來,與接受主體的譯者的感情脈搏發生共振共鳴,于是產生出多姿多彩的譯品。恰如許淵沖先生所說“原文越是模糊朦朧,譯文越可豐富多彩。”
我們不妨列舉一經典譯例,看看眾多譯本是如何從原作提供的意象框架和提示基礎上,在心靈中構建新的意象,產生不同的譯文:The Wine of Life keeps oozing drop by drop,The Leaver of Life keep falling one by one.(引自波斯詩人海亞姆的《魯拜集》第2首后兩句)
鶴西(程侃聲)的譯本:“生命的酒在一滴一滴地流淌,生命之樹的葉子正一片一片凋落飛紛。”
郭沫若譯本:“生命的酒漿滴滴地浸漏不已,生命的綠葉葉葉地飄墜不停。”
施穎洲的譯本:“生命之酒不斷涓涓滲注,生命之葉不斷一一飄淪。”
黃克孫的譯本:“酒泉歲月涓涓盡,楓樹生涯葉葉飄。”
李霽野的譯本:“生命瓊漿涓滴逝,人生綠葉漸飄零。”
譯文雖然豐富多彩,但孰優孰劣卻一目了然。這不僅體現了模糊性的魅力,同時也考驗著翻譯家個人的文學素養和語言功力。
從這個意義上講,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,文學翻譯是一門模糊藝術呢!
西安翻譯公司-首選西安亞達翻譯
聯系電話:、
雙休日及國家法定節假日:
業務洽談QQ:719183312、576408338
郵箱:(業務專用) (招聘專用)
地址:西安市蓮湖區北大街118號宏府大廈A座9層10922室